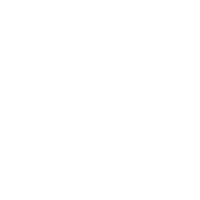2013年6月15—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启蒙与近代以来中国法治进程”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高校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利民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崔永东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近代以来中国法治进程的反思》。崔永东教授还做了题为《法治的基础是文化》的大会发言,北京大学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教授朱苏力先生对发言进行了评论。
崔永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法治与文化有密切关系,法治的基础就是文化。一个民族的法治如果不以该民族的文化为基础,那么这种法治是“无根”的,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飘萍”。一种游离于民族文化之外的法治是缺乏生命力的。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说过一句名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它随着民族精神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精神的衰亡而衰亡。”美国法学家霍姆斯也说:“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史。”这里所说的“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等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两位法学家的名言均揭示了法律与民族文化之间血肉联系,民族文化是法治的内生机制与内在动力,它赋予了法治的本质属性和外在风貌。
法治的重建需要文化的重建,文化的重建需要发挥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民族文化为主体(重在继承),同时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并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创新出一种新的文化。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孔子提到几个重要的概念:因、损、益。“因”指继承,“损”指否定,“益”指创新。这就揭示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否定不合时宜的成分,继承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并有所创新。
回顾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历程,是一个中华法系全面解体、中国法治逐步全盘西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只有否定,没有继承,也没有创新,只有“移植”(移植西方各国的法律,包括苏联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所谓法律体系,实际上游离于民族文化的母体之外,因而难免处于一种“虚悬”的状态——法律实施的效果令人生疑!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历程中,受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而是成了全面否定、大加挞伐的靶子,被当成了专制政治的附属物丢进了历史垃圾堆。其实,如果以理性的态度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绝非一无是处。就以受到批判最多的传统司法文化为例,其核心价值观是儒家的“仁道”,仁道即爱人之道,它强调尊重人、关爱人,特别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这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也存在着一些合理成分,这与儒家“仁道”司法观影响有关。例如,汉唐时期的“录囚”制度,它是一种由高官和皇帝复审案件以纠正冤假错案的制度,该制度在明清时期被“会审”制度所取代。显然,这样的制度在封建时代可谓善制。又如,封建时代的“直诉”制度是一种当事人可直接上访、上诉或起诉于中央的司法制度,对蒙受冤屈者能起救济的作用。再如,古代的赦宥制度是一种对重刑犯赦免宽宥的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减少死刑适用、减轻刑罚的作用。另外如“存留养亲”制度是一种对家无成丁奉养父母的罪犯进行宽宥的制度,该制度体现了某种人道关怀。还有如死刑奏报制度(唐代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说)、死刑监候制度(清代有“斩监候”、“绞监候”)体现了一种对死刑的慎重态度。
崔永东教授又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确有很多积极成分,但近代以来的知识界(尤其是“五四”之后)为何对其全盘否定呢?他认为这除了与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影响有关外,也与知识界所秉持的狭隘的法治观有关。人们不理解,历史上的“法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法治所依据的“法律”也是广义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谓“法律”除指国家制定法外,还包括礼仪、道德、制度、习俗等等,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其著作《政治学》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现代概念加以对译,最后发现中国古代儒家所说的“礼法”大致上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同义。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依“法律”为治的法治是广义的,那么儒家的“礼法之治”或“礼治”也是一种广义的法治。
另外,法治既是“国法”之治,也是“活法”之治。“国法”指国家制定法,“活法”指除国家制定法之外的一切有价值的社会规则。根据西方社会法学的观点,“活法”主要指道德观念、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调整社会秩序方面,它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国家制定法。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礼治既是国法之治,也是活法之治,而且特别强调活法的作用;而法家的“法治”则纯粹是一种国法之治,因为它排斥活法的作用。
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坚持了一种片面的“法治”观念,将法治简单地等同于“国法”之治,并将儒家的“礼治”当成法治的对立面加以抛弃,导致既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法律传统,又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法治的真精神。我们天真地认为,法治可以单纯依靠国家权力加以推进,而不是与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息息相通。如此一来,法治建设变成了国家权力场中的“仪式”和“作秀”,而不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于是,中国的法治进程流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同流沙之上的华美大厦,难免有坍塌之虞!
中国要想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需要重建中华法系,重建中华法系需要发挥中华民族的创制主体性。这种创制主体性是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兼采外来文化之优长(尤其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积极因素),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法律文化,构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
孔子曾总结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剔除文化传统中的的糟粕,继承其精华,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现代新儒学提出了“返本开新”的口号,“返本”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继承传统中的优秀内容;“开新”就是创新,即在吸收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缔造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且能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文化。
崔永东教授最后强调,“返本开新”应当成为我们重建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法系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