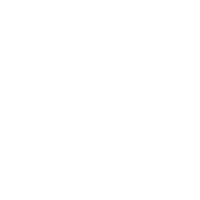2019年6月23日下午,“公法与治理”青年讲坛第十四期在研究生院科研楼A913会议室圆满举行。本次论坛由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行政法研究所主办,主讲嘉宾为郑州大学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郑磊副教授,论坛主题为“《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评注与反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毕洪海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伏创宇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所蔡乐渭副教授为本次讲坛与谈人,参加讲座的还有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行政法所张冬阳老师,以及来自校内外的学生三十余人。william威廉亚洲官方成协中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坛。

郑磊老师的报告主要讨论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立法形成、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解释和《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内涵变迁的制度反思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郑磊副教授从《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争议出发,提出应当对该条涉及的规则、学说和典型案例进行整理,以便为法律实践提供准确、高效的指引,同时也为行政复议法修改提供重要参考。

其次,郑磊老师追溯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形成过程。郑磊副教授认为,该条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4年之前,自然资源权属处理决定类行政案件未被明确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第二阶段是1994年《行政复议条例》修改之后,行政机关对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被明确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第三阶段是1999年《行政复议法》颁布之后,该法第30条正式确立了自然资源权属处理决定类行政案件的复议前置规则以及特殊情形下的复议终局规则。
再次,郑磊老师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5号批复、[2005]行他字第4号答复、[2005]行他字第23号答复为中心,详细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及其行政审判庭在解释《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过程中运用的解释方法和论证理由,并讨论了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解释的偏离,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25条对行政复议法第30条的发展与完善。

最后,郑磊老师提出,对行政复议法第30条进行法律重述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修法是解套之本。具体而言,在行政复议法修改过程中,应将30条第1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明确为“行政裁决”,将第2款中的征地决定是否可诉问题留给《土地管理法》和《行政诉讼法》解决。
近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之后,毕洪海副教授、伏创宇副教授、蔡乐渭副教授分别进行了评议,并分享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毕洪海副教授分享了四点思考:第一,关于主讲人梳理的法院对《行政复议法》第30条的解释,这是主讲人本身关于“法院为何这样解释”“采取了何种解释方法”的解读,而实际上法院的答复自身就应说理,而不简单地指示下级法院。第二,《行政复议法》第30条的解读,即判断复议终局或者复议前置的问题时应当考虑不同制度的功能设定问题,可以结合行政机关与法院所掌握的资源、程序条件和审查效果考察制度演进的逻辑;第三,主讲人所提到的无论是重述建议,尤其是第一款,虽然明确为“裁决”,但歧义总是会存在的,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学理上讨论的重点在于,不宜将法律上普通的用语简单转化为一种制度,行政行为类型化的方向应该看到其背后的制度功能,而非简单的分类。第四,法律解释的方法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解释者是谁,不能简单地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就解释方法而言,优先去看文本解释,并不代表文本解释的效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解释。

伏创宇老师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主讲人采取的整体法教义学方法,是一次很好的探索,其研究方法值得肯定;第二,从本篇报告的内容来看,针对某一法律条款的评注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报告的问题意识应当更加明确,还需要提炼出一个清晰的学术命题。

蔡乐渭副教授分享了三点思考:第一,从条文本身来看,行政复议法第30条的表述如此明确清晰,似乎并无解释的必要,但在实践中却如此歧义丛生,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法条的字面含义、法条的本意和法律适用之间差距如此之大?第二,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司法解释的功能。很多时候,最高人民法院不仅是在解释法律,同时还在创制法律。在法治体系尚不健全的时候,法院所发挥的“创制法律”的功能值得肯定。但是从长远来看,创制法律的角色不应当由法院来扮演,应当形成一个协调的释法体系;第三,报告人在结论部分提出修法是最终的解决之道,过于倚赖理想化的立法过程。

成协中教授总结了如下四点:第一,主讲人所展示的“法条—案例—文献”三步走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写论文做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只有在完成这三步之后,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第二,主讲人所采取的历史方法提醒同学们,在看法条、规范时不能想当然,不能只从法条本身出发,而是要重视法条的由来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第三,主讲人提到的“概念丛林”问题,可能主要不是一个立法能解决的问题。立法和行政实践中的概念必然是五花八门歧义丛生的,如何分析和归纳这些不同概念的法律意义,是学术界应当完成的工作。学界应当对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进行解释、归类,从而为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理论支撑;第四,主讲人通过历史地追溯以及考察不同部门的解释立场,来探寻第30条的真正意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其最后作出的“修法”的回应似乎过于迁就现实。在划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纠纷解决权限方面,应当重视不同机关背后的制度能力。无论是立法机关在立法中表达的立场,还是最高法院对立法的解释,都不能违背和超越不同机关本身的制度能力。法学的使命不应当仅仅是通过条理化的方式将既有规范整合,而更应揭示规范背后的理论与价值冲突,借鉴德国法上的功能适当理论来寻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权限分配的妥当路径。学者在其中可以而且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功能,而不是被动接受立法者、司法者已经表达的权限分配立场。
最后,讲座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